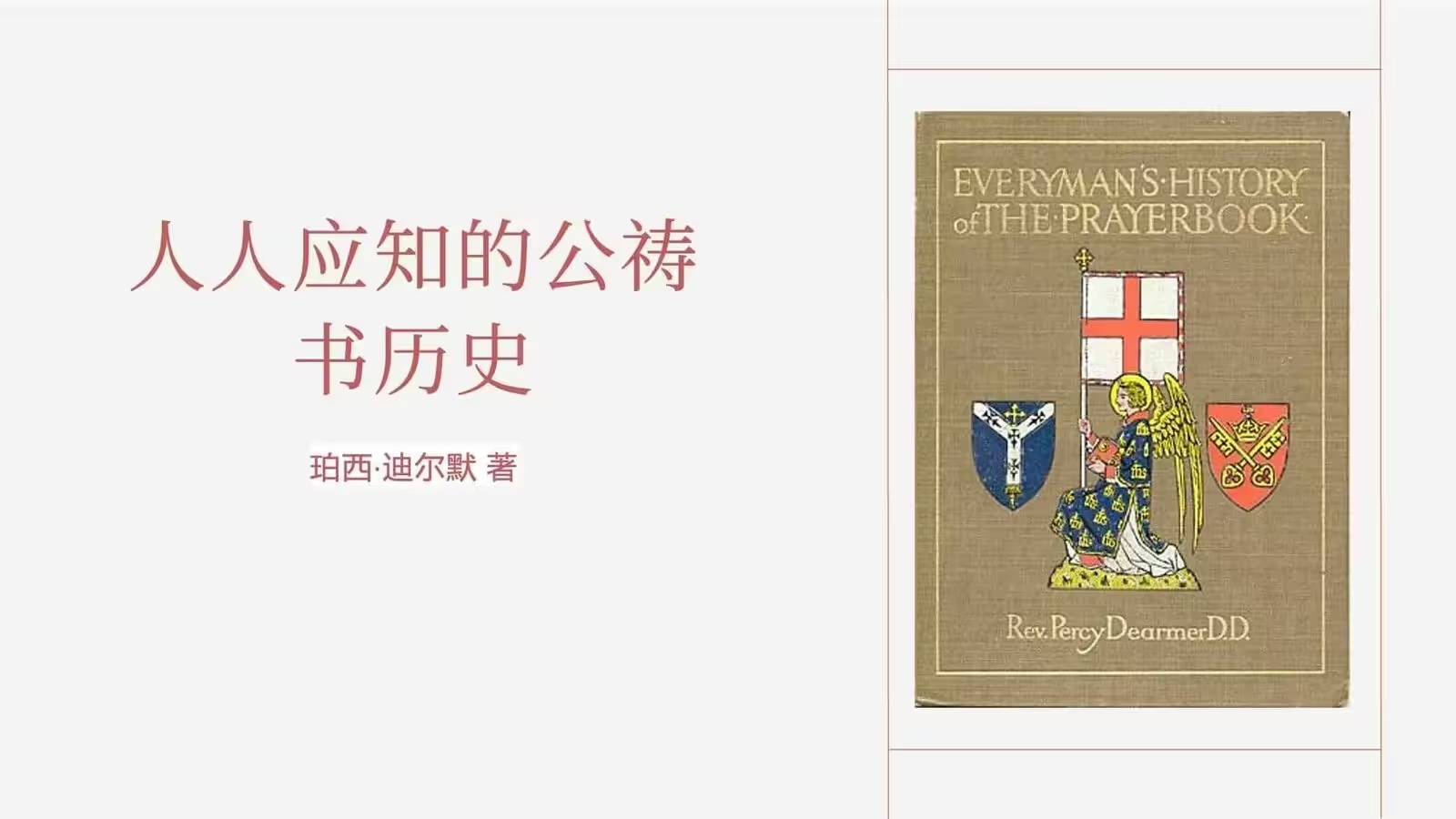
人人應知的公禱書歷史 第14章 聖餐禮
第14章 聖餐禮 珀西·迪尔默 聖餐禮不僅是基督教的核心與特有儀式,是最神聖的基督教奧秘,是基督徒生命中的重大聖事,是所有敬拜儀式中最簡單又最深奧、最精妙又最普及的,更是基督親自設立的唯一常規禮儀;或者更確切地說,它之所以具備這些特質,是因為它源自基督的設計,並且與洗禮這項偶爾舉行的儀式(另一項無疑是他所命定的聖事)一樣,都具有那種純樸與深邃相融的特質——一種取之不盡的簡樸性——這正是他所有言行的特徵,也確實是我們在宇宙中所知的一切偉大事物的特徵。 因此,本章的簡要概述必須從聖事的設立開始說起,正如記載於聖馬太福音(二十六章26-28節)、聖馬可福音(十四章22-24節)、聖路加福音(二十二章19-20節)和聖保羅書信(哥林多前書11章23-26節)。聖馬太如此記載:—— 耶穌拿起餅來,祝福了,就擘開,遞給門徒,說:「你們拿去,吃吧。這是我的身體。」他又拿起杯來,祝謝了,遞給他們,說:「你們都喝這個,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,為許多人流出來,使罪得赦。。」 上圖:聖路加福音標題(九世紀福音書) 我們從使徒行傳得知,門徒們認為這是一項「擘餅」的莊嚴禮儀的命令——「他們都專注於使徒的教導和彼此的團契,擘餅和祈禱」(使徒行傳2章42節),這禮儀是在家中舉行(使徒行傳2章46節),並在主日,即「七日的第一日」(使徒行傳20章7節)清早舉行,好讓他們能夠在非基督教世界之中白天仍舊能工作。這禮儀至少在這場合是由包含祈禱和講道的守夜禮拜所開始(使徒行傳20章7節)。在主日,每個人也要「抽出若干」幫助窮人(哥林多前書16章2節)。 從聖保羅的記載中,我們進一步得知,這聖餐被視為是表明主的死(哥林多前書11章26節),他們所擘得餅是領受主的身體,他們所祝福的杯是領受主的寶血(哥林多前書10章16節),若「不分辨是主的身體」就會招致極大的禍害(哥林多前書11章29節)。這裡還浮現一個禮儀上的事實——人們在「祝謝」之後都要說「阿們」(哥林多前書14章16節)。 因此,我們發現在使徒時代有一項莊嚴的每週禮拜,實際上是教會的禮儀,稱為擘餅禮。這項禮儀具有雙重特性。首先,它是一項奧秘的獻祭,是基督的獻祭的重現和參與(表明主的死),因此在公元150年左右被殉道者聖游斯丁稱為「獻祭」(the Sacrifice)。其次,它是與基督的身體和寶血的共融,因此早期被稱為「共融」(the Communion,),這是遵循聖保羅的「豈不是同領」等說法。聖保羅所用的「感恩祭」(Eucharist)一詞,即“感恩”(thanksgiving),雖然他並未將感恩祭或共融作為禮儀的正式名稱,但這稱呼很早就被採用了,這可能是因為它重現了基督在最後晚餐時的祝謝。普林尼使用聖事(sacrament)一詞(公元112年),他可能是從基督徒那裡聽來的,但並不理解其含義,無論如何他只是將其用作誓言或承諾的意思:九十年後,特土良稱這禮儀為「聖事」。後期拉丁文中表示解散的詞——彌撒(missa),使得這禮儀在西方最早在385年就被稱為彌撒,而在東方通常被稱為聖禮儀(Liturgy),這個名稱最初是用於任何公共禮拜。 上圖:戈登聖爵。一個黃金聖杯,現存最古老的聖爵,可能製於公元527年之前。 擘餅禮與一種社交性的“餐會”或“愛筵”有關,通常稱為愛加倍(Agape),但聖保羅稱之為「主的晚餐」,這名稱在中世紀有時也用來指彌撒本身,宗教改革者們也經常使用這稱呼。若不是因為其濫用的情況,我們根本不會知道使徒時代有這種愛筵——因為最普通的事物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而不被提及:這些貪婪無度之人對愛筵的濫用被聖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1章20-22節中提及,其他作者在彼得後書2章13節和猶大書13節中也有提到。在普林尼的記載中,提到禮拜之後有「簡單純潔的餐食」(common meal of innocent food);這不可能是聖餐禮,因為基督徒在被下令禁止集會得時候,就放棄了這做法。在公元200年之前,正式的愛宴就已消失,只是作為窮人的慈善餐會,以及在葬禮或追思禮拜之後的追思餐會而延續到五、六世紀。這個概念在東方教會仍以祝福麵包(譯者注:東正教的祭臺上會方很多個麵包,當祝聖聖體血的時候,選擇其中一個,剩下的作為祝福主後的麵包分給所有的人)的形式存在,在英格蘭直到宗教改革時期也有分發,如今在許多法國教堂仍保留為pain bèni(祝福麵包)。或許有人希望在當今的英格蘭能重新恢復主日的友誼餐會。對於早已脫離異教的民族來說,一場社交茶會不會被濫用,而這樣實踐基督徒團契的功課是非常需要的。 接下來關於感恩祭的記載來自普林尼,他作為一位異教徒,羅馬帝國的總督,在公元112年左右從他治理的比提尼亞省向圖拉真皇帝發出以下報告。雖然這份描述難免帶有局外人的模糊性,但它仍然彌足珍貴,因為它展現了基督教在一個野蠻、盜匪橫行的地區初期發展的景象:— 「他們承認他們唯一的過錯或謬誤就是:他們習慣在固定的日子、天未亮的時候集會,輪流唱頌讚美基督如同讚美神明的讚美詩;並且他們以莊嚴的誓言(sacramento)彼此約束,不是為了犯罪,而是要戒絕偷盜、搶劫和通姦,要信守諾言,並且不得拒絕歸還寄存物。做完這些之後,他們就散去,之後再聚集共享一頓簡單純潔的餐食(common meal of innocent food);但就連這個,他們說,在我按照您的指示頒布禁止結社的法令之後,他們也已經放棄了。」 上圖:二世紀的聖餐禮(普莉西拉地下墓穴中的壁畫) 幾年前,威爾佩特在羅馬聖普莉西拉地下墓穴的一座小教堂牆壁上,發現了一幅極其有趣的聖餐圖畫,其年代與前述時期相同(介於公元100年至150年之間)。這幅畫現在被稱為Fractio Panis,即擘餅禮。主教或主禮(身著代表身份等級的pallium長袍和內袍)坐在桌子的一端正在擘餅,桌子周圍還坐著五位男子(只穿著內袍,沒有pallium長袍)和一位婦女。桌子上鋪著亞麻桌布,可以看到一個雙耳杯和一個盛有五個小麵包的盤子。還有一個盤子裡放著兩條魚——這是當時常見的基督象徵,在這些早期地下墓穴的畫作中,它們神秘地連結著給群眾分餅、聖餐禮,以及洗禮。因此,我們在這裡看到了一幅原始聖餐禮的圖畫,展現了當時在這地下小教堂中實際舉行的情況:石凳仍然存在,還有一個小墳墓,大小僅能容納為數不多的殉道者聖髑,不過原本應該用作祭壇的石板現已不復存在。 接下來的記載非常重要,因為它為我們提供了大約公元150年左右禮拜儀式的清晰框架。這是殉道者聖遊斯丁在他給安敦尼·庇護(Antoninus Pius)皇帝的護教書中所寫,因此使用了異教徒能夠理解的措辭,例如把主教稱為「主席」(the president)。我們逐字記錄下來,只是將其分成幾個部分,以展示當時禮拜儀式的基本結構已經確立。當然,這些標題並非原文所有。我們將遊斯丁的概述與杜謝恩(Duchesne)從兩個世紀後的敘利亞文獻中整理出的更詳盡記載並列呈現,那時迫害的日子已經結束,基督教也已被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繼任者所接納。 當然,在第二世紀到第四世紀之間,禮儀逐漸發展;習慣演變成固定的儀式,傳統也更加明確地規範了主禮人祈禱時應遵循的界限,儘管實際使用的禱詞要到大約一個世紀之後才普遍固定下來。 上圖:六世紀的主教。聖艾克勒修斯身著襄祭批(Dalmatic)帕努拉(PAENULA,祭披的前身)及白羊毛披肩(Pallium)的馬賽克畫像。 上圖:白羊毛披肩(Pallium) 關於這兩個時期之間的禮儀,我們所知不多,但有幾個要點值得注意。從特土良的記載中得知,大約在公元200年,禮拜如同普林尼時代一樣在天亮前舉行。希波呂陀的《法規》( The Canons of Hippolytus),大約在第三世紀中葉,告訴我們(正如我們從這個早晨時段所能預期的)領受聖餐時必須禁食,而且主教、司鐸和執事都穿著白色禮服,「比平信徒的衣著更為華美,盡可能莊嚴」,誦經者也要穿著節慶禮服:我們也知道當時常用的禮服包括dalmatic、帕努拉(提摩太後書四章13節中提到的外衣(phaelonen),後來稱為祭披),以及主教披肩,因此聖職人員和會眾的外觀與上方圖片所暫時的相似。我們還得知,感恩經(the Canon,使用後來的稱法)如今一樣始於心中仰望問(Sursum Corda,願主與你們同在。願主與你的心靈同在。你們心裏當仰望主。我們心裏仰望主。我們當感謝我主上帝。感謝我主上帝是應當的。)。這些禮規還告訴我們,送聖體時所用:「這是基督的身體。這是基督的血」,領受者每次都回應「阿們」。我們還從中得知,奉獻禮包括獻上穀物、酒和油,並為此獻上感恩。 殉道者聖游斯丁 敘利亞文本 一、慕道者禮儀 一、慕道者禮儀 1、預備 1、預備 經課 「在稱為主日的那一天,無論是住在城鎮或鄉村的人都聚集在一起,誦讀使徒的回憶錄或先知的著作,時間允許的話就多讀一些。」 經課 在教堂中央附近的讀經台或講台上誦讀兩段經課;然後另一位執事登上讀經台詠唱詩篇。接著繼續誦讀其他經課和詩篇,最後總是以福音作結,福音由司鐸或執事宣讀,期間全體會眾起立。 證道 「當誦讀完畢後,主禮者會以教導和勸勉的話語,鼓勵大家效法這些美善之事。」 證道 眾司鐸中願意講道的都可以講道,之後是主教講道。他們通常的座位環繞在後殿周圍,面向西方,主教的座位在正中間,緊靠在祭壇後方。 遣散與連禱文 候洗者、被逐出教會者、懺悔者和精神病患者被遣散,執事(在靜默祈禱後)為他們作連禱,信眾則回應「求主憐憫」(Kyrie eleison)。所有可以領受聖餐的基督徒則留下。 二、信友禮儀 二、信友禮儀 2、奉獻禮 2、奉獻禮 祈禱 然後我們一起站起來做禱告。【在另一處——「為我們自己、為受洗的人,以及為各處的所有其他人一同禱告,使我們既然已經學習了真理,也能藉著我們的行為被視為良好的公民和遵守誡命的人,好讓我們得著永恆的救恩。】 連禱文 執事為世界、教會、神職人員、病患、兒童等誦讀連禱文:會眾在每一個祈求後回應「求主憐憫」(Kyrie eleison)。之後主教進行莊嚴的禱告。 平安之吻(在此或之後) 在他的《護教書》的另一部分中,游斯丁提到和平之吻是在禱告和奉獻禮之間——「當我們結束禱告時,我們以親吻彼此問安。 平安之吻 主教親吻其他神職人員:會眾中的男性信徒彼此親吻,女性信徒也彼此親吻。 獻禮 當禱告結束時,餅和酒與水被帶上前來。他在另一處這樣寫道:『餅和摻水的酒杯被帶到弟兄們的主禮者面前。』 獻禮 執事看守門口,並安排會眾就座,讓孩童坐在最靠近聖所的地方。其他執事將餅和聖爵帶到祭台上並放置其上,其中兩位執事揮動扇子驅趕蒼蠅。主教洗手並穿上節日禮袍。 3、感恩經 3、感恩經 感恩經 需要記住的是,游斯丁並未提供細節。上文中的「感恩」在希臘原文中是eucharistias。這個詞也用在比游斯丁更早的《十二使徒遺訓》(約公元90或100年)中,其中給出了一個簡短的程式:「關於感恩(聖餐),你們必須這樣做。首先,為聖爵:『我們感謝你,我們的父,為你僕人大衛的聖葡萄樹,就是你藉著你的僕人耶穌使我們認識的。願榮耀永遠歸於你。』為擘開的餅:『我們感謝你,我們的父,為生命和知識,就是你藉著你的僕人耶穌使我們認識的。願榮耀永遠歸於你。正如這擘開的餅曾散在山上,如今卻被收聚合而為一,願你的教會也如此從地極被收聚進入你的國度,因為榮耀和權能都是藉著耶穌基督永遠歸於你。』」 感恩經 主教畫十字聖號並祝福。 心中仰望文(「你們心裡當仰望主」等)。 序言和三聖頌。感恩禱文的第一部分(現稱為序言,紀念上帝的本性和創造之工,最後以三聖頌「聖哉,聖哉,聖哉」等作為高潮)。 感恩禱文的延續。主教(總是用自己的話)紀念上帝在救贖中的工作和基督的生平,引向建立聖事敘述(包括「這是我的身體」等),之後是紀念,即紀念主的受難、復活和升天。 求聖靈降臨。主教祈求聖靈使餅和酒成為基督的身體和寶血,從而完成祝聖。 「會眾以『阿們』表示同意。」 代禱。感恩禱文(The Eucharistical Prayer)以為生者和亡者祈禱作結。然後會眾說:阿們。 主禱文,隨後是一段簡短的執事連禱。主教祝福領聖餐者。(擘餅禮,即分餅,無疑是在此時或在Sancta sanctis之後進行。) 4、聖餐 「已經祝謝過的聖物被分發,使每個人都能領受。【他在另一處說:『當主禮者祝謝完,所有會眾都表示同意後,我們所稱的「執事」將餅和摻水的酒分發給每位在場的人,這些聖物都是已經祝謝過的,他們也會把一份帶給那些不在場的人。』」】 4、聖餐 邀請文 主教呼喊:「聖物歸聖徒」(在古拉丁禮儀中為Sancta sanctis)。會眾回應:「惟獨一位為聖,惟獨一位是主……榮耀歸於至高的上帝,在地上平安……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……和散那歸於至高。」 全體領受聖餐;首先是主教,然後是司鐸、執事、副執事、誦經士、歌咏士、女執事、童貞女、寡婦、小孩,最後是其餘的會眾。他們用右手攤開接受祝聖過的餅,左手托著,主教說:「基督的身體」;他們從聖爵中飲酒,由執事執行分送並說:「基督的寶血」。每個人都回應:阿們。同時,詠唱員唱詩篇第33篇。 感恩與遣散禮 主教以全體的名義做感恩禱告,然後祝福會眾。執事說:「平安散會。」 保留聖餐與施捨 ...